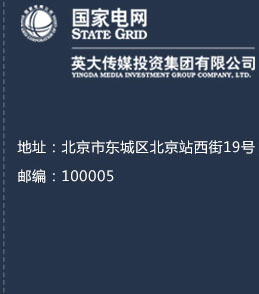大别山人家

供电员工向村民了解用电情况。 桂婧文 摄
大暑节气过后的一天,我和朋友登上鸡鸣石。那一刻,眺望四周层峦叠嶂,顿觉心旷神怡。迎着清爽的风,我感觉到了丝丝凉意。
这里位于大别山中心地带,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一处高峰之巅,群山苍莽,层峦叠翠,峰高崖陡。峰顶安放了一块有着三个面的水泥块,每一个面用红漆标注了一个省的名字,面向三个方向:东面是安徽,南面是湖北,北面是河南。
村庄在山坳的绿树间若隐若现,恍如画师不经意间洒落的几点彩墨——红的、白的、蓝的、黄的,静静地镶嵌在这幅巨大的画卷中。
我走进画里,走进大山深处的山水绿树间,体验大别山人家的寻常生活。
一
走下鸡鸣石,我们乘坐的汽车一头钻入无边的深山老林中,恍如一条小鱼游进了广阔的大海。远处的青山,近旁的庄稼,都生机盎然。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坎,绕过了多少弯,车子终于停在画卷中的一个名为白垄的小墨点里。
白垄是河南省商城县长竹园乡王畈村的一个村民组。村口有家小超市,一个中年女人正忙着招呼顾客。她面庞黝黑,笑容恬淡,短发齐肩,梳理得整整齐齐,拢到耳后。
有人喊她苏莉。我知道苏莉这个名字,是因为看到了她家那栋精致的三层楼的一楼墙壁上,表箱里的电表屏一侧写着“苏莉”二字。电表下方,还有一个充电桩。充电桩上绿灯闪烁,表明它可以正常充电。
“你家的新能源汽车呢?”我问。
“我老公开走了,去麻城了。”苏莉说。白垄离湖北省麻城市30多公里,苏莉的丈夫在麻城务工,每天早出晚归,开车方便。
攀谈中得知,苏莉出生于1980年,娘家位于麻城市三河口镇九歇山村,离白垄只有两三里路。20多年前,当她嫁到白垄时,丈夫家的小超市就开起来了。当时供电不稳定,一遇到刮风、下雨或打雷,就会停电。这对超市里的冷冻食品来说是个大问题。他们不得不购买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
21世纪初,九歇山村实施电网改造,连带着给白垄的6户湖北籍人家牵了电,还把20多户河南籍居民的用电难题也解决了。他们的用电价格跟湖北籍居民的一样。几年之后,河南这边实施农网改造,白垄的湖北籍人家又自愿接入了河南电网。供电员工将河南和湖北的供电线路接到了同一个电闸上,一推一拉即可切换。
说到这里,苏莉十分感慨:“湖北和河南两边不可能同时停电,我们再也不愁没电用了。”十几年前,苏莉家门前修通了水泥路,村民家中电器数量增加。渐渐地,很多人家买了新能源汽车。大约六年前,河南这边的供电公司为白垄专门装了一台变压器,村子的供电可靠性更高了。此后,苏莉家的那台柴油发电机再也没有启动过。
同行的来自商城县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儿。
三年前的春天,鄂豫皖交界处三个供电所的党员代表齐聚一堂,签署“鸡鸣三省”支部结对共建“供电服务根据地”协议。协议规定,三省交界处的群众和企事业单位有任何用电需求和困难,打任何一个供电所的电话,三个供电所都无条件提供帮助,绝不推诿。
我坐在小超市门边,吹着风,十分凉爽。小超市旁边的一条小街道把河南的王畈村和湖北的九歇山村连接在了一起。
二
一辆小汽车从远处驶来,停在门前的树荫下。车上下来一个男子,黝黑的脸庞上泛着汗光。苏莉出门打招呼,请那男子进屋喝杯茶水。
男子名叫罗余良,是王畈村党支部书记,1972年生人。他以前长期在外打工,2016年回到村里工作,2020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罗余良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两年,王畈村修建了13口大塘,还在灌河的一条支流上修筑了两道坝埂,形成了河堰,村民浇地不再愁;村里开垦了200多亩撂荒地,种植水稻、玉米、大豆、红薯;今年,村里还计划将村组道路由目前的3米拓宽至5.5米,解决村民开车出行会车困难的问题。
话音未落,罗余良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九歇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元志打来的,说是要协调两个村的一些问题。他当即赶往九歇山村。我也和他一起过去。
九歇山村和王畈村曾经都是深度贫困村,整村脱贫后,村民生活水平渐渐提高。
陈元志说,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如何带领村民致富至关重要。他掰着指头细数起村里的产业项目,比如生态水稻、油茶种植,玉竹和黄精等中药材种植,以及光伏电站。除此之外,村里还有70万元的产业帮扶基金,每年可分红7万多元;另有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50万元,投资到一家农业公司,每年可分红2.5万元。
九歇山村存在季节性缺水现象。当地政府和自来水公司共同出资建设饮水工程,给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管。眼下,饮水工程主体已竣工,年底可投入使用。陈元志说:“这次安装自来水,我们对河南籍的村民一视同仁。”
九歇山村村民早在1986年就开始使用大电网供的电,只是遇到打雷、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常常会停电。2006年,农网改造升级后,村里的停电次数大幅减少。去年,供电企业再次改造升级农网,为九歇山村增加了两台变压器,从那之后村里再也没停过电了。
如今,九歇山村的水、电、路都已修好,塘堰河堤也已改造完毕,人均年收入超过1.2万元。陈元志还想发展村里的饮食文化项目,提出“吃在九歇山,玩在黄柏山”的乡村游设想。
黄柏山,就是紧邻湖北麻城市和河南商城县的国有黄柏山林场。鸡鸣石就在黄柏山林场的东南角。
三
车子沿蜿蜒的山路爬上卧牛岭,是在翌日上午。太阳炫目,漫山树木郁郁葱葱。
卧牛岭是一道山岭的名称,也是商城县伏山乡簪子河村的一个村民组的名字。一岭分两省。卧牛岭东是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上畈村圣塆村民组。
卧牛岭上有一户人家,为安徽籍,门外挂着豫皖生态养殖场的牌子。
我走进院中,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正坐着拔鸡毛。她叫杨荣平,是养殖场老板,一早有人打电话要买两只鸡和五只鹅,她正忙着准备。一只母鸡售价120元,鹅的价格是一斤30元。她家也是河南和安徽的电都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她家的用电量也越来越大,已经向河南这边的供电所申请了三相电。供电员工回复,电杆已经架到了岭下,再栽一基电杆就能牵过来。
告别卧牛岭,我继续往东,在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县沙河乡祝畈村吴冲村民组见到了一个名叫江咏梅的女人。她也是养殖户,养的是娃娃鱼。
江咏梅递给我一个手电筒,带着我往养殖娃娃鱼的地下室走去。手电光所照之处,是一个个水池,每个都是两米见方,足足有二三十个,布满一百多平方米的地下室,中间只有一条逼仄的通道,通道两侧还有更窄的小水沟,连通着所有的水池。水池都由混凝土砌筑而成,壁高过膝,池内养的就是娃娃鱼,总计两万余尾。娃娃鱼现在在市面上一斤能卖到150元。
四周青山叠翠,云白天蓝,蝉鸣声不绝于耳。抬头望去,头顶的电线从外面凌空飞进小院,江咏梅说那是三相电,2017年牵来的,这七年,她从没为用电发过愁。
“我们这里环境好,村民组都没有迁出去。”江咏梅说,“我们靠养殖娃娃鱼,每家一年收入十多万元,生活十分满足。”
我辞别江咏梅,来到几百米外的一户人家。
一座两层小楼前,一对老年夫妇正在水龙头下洗东西。户主名叫李志华,出生于1967年,有着古铜色的皮肤。
我见他家堂屋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遂问:“你喜欢拉二胡吹笛子吗?”李志华腼腆地摆摆手,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做不了,手坏了。”他让我看他的右手食指。
几年前,李志华外出打工做汽车油封时,一不小心,右手食指被切断了。断指接上了,却不便弯曲。他回到了家乡,把二胡和竹笛挂在了墙上,再也没碰过。这个故事令人唏嘘。
如今,李志华在家种植了四亩水稻、两亩天麻、两亩黄精和四亩核桃,一年收入能有六七万元。农闲时节,他会骑上摩托车,去黄柏山采摘金蝉花,拿回来卖钱。“以前两个女儿上学,我家日子紧紧巴巴。现在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在合肥工作成家。我啥都不愁,非常满足。”李志华感慨道。
四
火红的落日渐渐沉入西面的大山,道道余晖涂抹在东面的山峰上。望着余晖勾勒出的山峦轮廓,我知道那里是太阳歇息的地方,是李志华常去采金蝉花的地方,也是陈元志说的“玩在黄柏山”的地方。
那里是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茫茫林海。
车子行驶在大别山深处,忽高忽低,左晃右摇,恍如一只小舟颠簸于茫茫大海上,时而被抛上波峰,时而又被抛入浪底。四周鸟鸣声不绝于耳。
暮色中,我偶尔会看到高架路桥在我上方凌空飞过,那是正在建设中的环大别山高速公路。这条路预计在今年国庆节前后通车,将把处于大别山中心区的鄂豫皖三省有关县市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时,从商城县城到麻城市区或金寨县城,只需半小时车程。
回来后过了许多天,我的脑海中仍会浮现出探访大别山人家的一幕幕场景。闭上眼睛,那一张张真诚而朴实的面庞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那几天,我在行车途中看到了闪现的烈士墓和纪念碑,还有很多红色遗迹。
在黄柏山的青山绿水间,我见到了一处烈士墓。碑文记载着方永乐烈士牺牲时,年仅20岁,担任的是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委。
在三河口镇,我听到了九歇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的故事。1948年春天,刘邓大军的一支部队在九歇山凌家塆后山与国民党军队主力遭遇,发生了一场激烈战斗。我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转移休整期间又遭敌人炮火攻击,百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场面极为悲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修建了纪念碑,纪念先烈。
金寨县的红色遗迹更是数不胜数。在革命斗争中,十多万金寨儿女参军征战,血洒疆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超过一万人。他们的流血牺牲,正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夜宿山中时,我登高眺望,只见茫茫夜色中,散布于山林间的灯光犹如天上的星星洒落人间。
我又想起了那个年轻人,他是金寨县沙河乡高牛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年轻人名叫严锐,出生于1987年。他的话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他说全村共有386户1410人,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村里开办有竹制品加工厂、养蚕室、手工挂面厂、春茶厂,村集体年收入72万元,在全县200多个村中排名前二十;村里用上了三相四线的电,村部前面有一大片太阳能光伏板,所发的电不仅够他们自己使用,余量还能送入大电网。
能够列举的事例还有很多。但当时天色已晚,我只得向严锐挥手告别。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那认真专注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