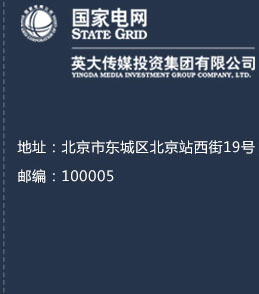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向光前行·我和祖国共奋进”征文|梅岭灯光
龚家凤
我出生在江西南昌湾里区一个叫桐源的小山村。桐源村位于梅岭山区。梅岭群峰拱秀、奇岩突兀、秀竹满山。记忆中,桐源村屋舍分布在山间,高低错落,密密匝匝。村头村尾,树木参天,夏日里,整个村庄凉森森的。
20世纪60年代末,桐源村村民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些个不眠之夜,乡亲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说着城里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生活。山外有一种叫“电灯”的东西,不用油,只要两根线连着就能发光。
记得1969年的农历除夕,我们一家人坐在堂屋里烤炭火。油灯把我们的影子映照在墙壁上,影子老大老大,一晃一晃的。那天,父亲没有给我和侄子秋生讲故事、唱歌谣,而是兴致勃勃地说起桃花庄姑姑家通电的事。他还说,山里每天只能见到一块巴掌大的天,初二带我和秋生去姑姑家拜年,见见世面。
桃花庄在山外,要走二十多里山路才能到。我们叫山外的人“坪下人”,他们则叫我们“西山岭里人”。那天,天才蒙蒙亮,父亲和大哥把我和秋生各装进一只箩筐里,将箩筐挂在扁担上。山路弯弯,扁担弯弯,父兄轮流挑着,一路迈着大步。两只箩筐在路边青草中划过,就像两只乘风破浪的小船。
到了姑姑家,我发现她家堂屋中央挂着一个小葫芦似的东西,我愣愣地看着。姑姑一拉开关,小葫芦霎时发出了耀眼的光。父亲说,那就是电灯,我惊讶极了。电灯要比油灯亮上十倍百倍啊!我和秋生高兴得在屋里屋外上蹿下跳,还不时拉灯取乐。姑姑送给我两只旧灯泡。回家后,我从菜园里砍来棕叶,撕成丝,将棕叶丝连接起来,从自家拉到邻居家,学着“架电线”。我又把旧灯泡挂在自家堂屋梁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
20世纪70年代初,我六七岁时,梅岭很多地方建了发电站。刘家姑姑住的南源村就建了发电站。一天,母亲带我去刘家姑姑家做客。一到姑姑家,我就迫不及待拉开关,灯泡并没有亮。姑姑说,要等到晚上七点才发电呢。姑姑一双小脚,走路摇摇摆摆,硬要带着母亲和我去看发电站。我们跨过村前的溪流,沿着一里长的水渠来到半山腰,看到一个蓄水池。水在这里积蓄力量,再顺着水渠俯冲而下,冲击水轮机发电。
一直到了21世纪初,湾里区修地方志,我要写当地供电发展史,才知道湾里区从1969年开始建梅岭、罗亭、立新、南源四座水力发电站。四座发电站差不多到1971年年初才全部发电。梅岭、罗亭、立新都只有两台发电机组,总容量140千瓦,可供七八千户照明。而南源仅有一台发电机组,容量40千瓦,供两三千户照明。这些发电站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停运。
那一天,我在刘家姑姑家住。比我大50岁的大表哥晚上打着火把,带我走五六里山路,爬上村前的高山去看南昌城的灯光。一路上,附近村落的灯光透过林梢照过来,忽明忽暗的。我们到了山顶朝东南望去,只见南昌城灯火璀璨,好似星河。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电如此神奇啊!
不久后,汽车开进了我们村。紧接着,村里来了架线工。就在我九岁那年,桐源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村里送电那天的傍晚,乡亲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
1999年12月,湾里区供电公司挂牌,从那时起我就在这个单位从事宣传报道工作。我用一行行文字、一张张图片,记录了湾里区架起的每一条线路、投运的每一座变电站。2000年以前,梅岭山区电网十分薄弱。在电网改造升级的那些日子里,湾里区供电公司全体员工每天都起早摸黑去现场,奔波在梅岭的崇山峻岭中,天晴一身汗,落雨一身湿。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他们将电网建设一新。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008年,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苦干了一个多月时间,以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将因冰雪灾害受损的电网全部修复。
如今,假如你行走在梅岭的山路上,可能会遇见我的同事,他们身穿工装,来去匆匆。山里村庄现在多是老人、小孩居住。一次漏保跳闸、一只灯泡烧坏……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我很幸运,在我有记忆的50多年里,切身感受到了家乡梅岭山区的发展与变化。如今的父老乡亲,不仅用电来照明,还用电来发展生产,创造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