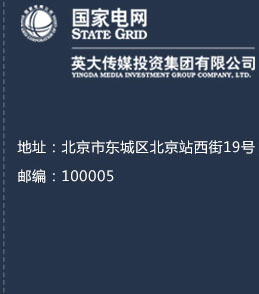重读《刀锋》的理由
重读《刀锋》的理由
文/阿光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舍友从图书馆回来,激动地说:“我今天看了一本非常好的小说——毛姆的《刀锋》,简直太好了,太好了。”她一边说,一边喃喃地赞叹,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很受触动,也跑去看了,翻开扉页便被卷首语吸引住了:“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这句话蕴含着广阔而深奥的智慧,一时间超出了我十几岁的头脑所能理解的限度。
《刀锋》刻画了一个物质和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故事的核心人物拉里以其遗世独立的形象,成为弃绝物质享受、一心叩问生命本质的代名词。相比之下,追求享乐、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一心往上爬的芸芸众生所构成的另一个世界,则显得贫乏而可笑。对年轻的我们来说,拉里无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那时候我们站在成年人世界的门口,一边想征服它,一边又带着极大的蔑视,认为门后的世界里有种种陈规陋习正等着我们去改造,即便改造不成,至少我们也能轻松跨越,不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尤其是读到拉里讲述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时,那种自由洒脱的人生态度,又何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今年,《刀锋》出了新译本,隔着二十年的距离,我又读了一次。以往被掩盖在尘埃中的另一个世界,那个被我们迅速抛在一边的纸醉金迷的现实世界,突然露出真切的表情。
这个世界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艾略特·坦普尔顿的男人,他是一个美国人,在这个新兴国家依靠种种不可名状的手段发了家,从此便开始了在欧洲社交圈的历险。社交就是他的命根子,他人生的全部价值感都来自于结交了某个贵族、伯爵,甚至是女王。这个新大陆的来客并不缺乏文艺气质,他是欧洲上流社会的艺术顾问,也是他们的投资专家。跟所有交际花一样,他趋炎附势,无比势利,见人下菜碟的功夫简直可称精准。这也是一个由大量物质细节堆砌起来的人,他别针的材质、柜子的样式、佐餐的葡萄酒,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就是从艾略特这里领略到了一种名叫蒙哈榭的葡萄酒,乃至当他亲自看到这种酒的时候,也有了一种跻身上流的幻觉。
这就是艾略特的吸引力。他对生活饱满的热情、他的缺点和可笑之处能让我们迅速记住他。有一点很多人提到过,也是我此次重读的深刻感受,那就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看,艾略特比拉里成功得多。对比艾略特的虚荣、狡猾、矛盾,拉里的理想主义显得轻飘飘的,并没有太多生活细节的支撑,因此也显得多少有些不可信。他那大段大段的讲述经常让人走神,我们看拉里,始终像看一个地平线上的影子,而艾略特就坐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用他的一举一动演绎着一种无论何时何地都并不罕见的人性。那种熟悉的感觉,几乎能让读者感觉温暖。
最重要的是,二十年后再看,拉里和艾略特体现出了相似的悲剧特征。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探索人生的轨迹也多有重合之处。他们都不喜欢当时美国社会的蛮荒和无知,要去欧洲寻求更深层次的认同。艾略特周旋于上流社会,但那些王子、伯爵、贵族最终将他遗忘;而拉里尝试了科学、艺术、宗教等诸多解决方案后也未能如愿,最终去了印度。在这期间,美国经历大萧条,欧洲则隐隐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也就是说,他们都身处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他们的追问都是时代症候的某种象征。最终,当艾略特垂死病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归宿指向了宗教所能提供的永恒,而永恒,正是拉里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反过来,理想主义者拉里也并不鄙弃现实,他始终行走在人群中,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与他们的生命发生深刻的碰撞。他从吠檀多不二论中获得的教益是:它不会硬要你相信任何事,它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全身心地渴望了解现实。“你可以通过知识捕捉现实,我觉得这种想法妙不可言,让我极为满足。”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回美国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一滴水般汇入了人群。
通过这次重读,我对毛姆的看法也改变了。以往人们总说他“刻薄”,但我发现他非但不刻薄,反而比其他作家拥有更多的包容性。他尊重自己的每个人物,并不强硬地改造他们,而是允许他们固执己见、一条路走到天黑。他还为他们各自安排了妥善的结局。毛姆本人无疑是个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尽管他也通晓其浅薄无聊之处,毫不留情地取笑每个人,但其实在他笔下,所有人都和艾略特一样,“他的缺陷都在表面,他的心是很宽厚的,对他人满是善意。”无论一个人追寻的是什么,过程都同样艰难,而结局,都同样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