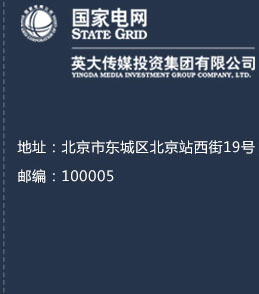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文/司空
每次回到浙东天台县,都能体会到家乡人在吃上面深刻、深沉、深入骨髓的自豪。
姑姑总会做上各色家乡小吃,然后用怜惜的眼神看着我埋头大吃,不时会问:“杭州没这个吧?吃不到这个吧?”仿佛我在杭州基本上就是勉强维生的状态。
要说食饼筒、麦饼、扁食之类天台特色的小吃在杭州难得吃到,那是事实。但是吃年糕的时候也这么问,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呢?“不,外地那种年糕能叫年糕?能有天台水糕好吃?”家乡人称年糕为水糕,捣水糕时加的粳米更多,成品更硬实,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吃惯了扎实水糕的天台人再看其他地方那些偏软糯的年糕不免带有俯视眼光。不过天台水糕太过硬实,切时极费力气,要双手扶刀,踮起脚,将全身重量压在刀背上才能切开。每次切完,双手总是压得通红。
婶婶说,杭州真没什么东西可吃,还是天台的东西好。某位亲戚在杭州生意做得也不小,每个礼拜回来,还是会满载一后备箱的家乡特产回去,连酱油都要在天台买了带回去。
大哥打开我的汽车后备箱,把给我带的东西一袋一袋往上拎:豆腐皮——豆浆煮得甚是浓郁,揭出来的腐皮又厚味道又正,带上;面干——就是米粉干,全部是纯手工日晒制成,带上;豆面——也就是粗粉条,外地都没有豆面,带上带上。甚至,这个街头菜刀好,切菜飞快,大哥也给我买了两把,一并带上。
就像天津人总觉得煎饼馃子只要一出天津地界,立马变得面目全非。郭德纲把这事编进相声里,在舞台上夸天津的煎饼馃子:“面是绿豆面、黄豆面、小米面、白面、棒子面按比例掺合在一起,用羊骨头熬的清汤和面。现炸的馃子一尺长、枣红色,炸出来卷上,你就吃去吧。”北京也有煎饼馃子,“咬一口粘上牙膛,咽不下去,拿棍子往下捅”。这个连损带鄙视的劲儿里更多藏着的是对家乡食物的自豪。
汪曾祺也是如此,写家乡高邮的特产咸鸭蛋,自己是很不在乎地说“还不就是个鸭蛋”,甚至“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但可真要和别家的去比,那就不是这样了,“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
家乡是所有人的来处,家乡总是好的、熟悉的。有首歌里唱着“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够的家乡水”。更何况是家乡的食物,那是在成长的岁月里,浸润了味蕾,渗透进记忆,有时候还夹杂着某种情感、某段故事,酝酿成为独一无二的味道,其他地方的食物哪能与之相提并论。鲁迅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虽然是人间清醒,也逃不过对家乡味道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