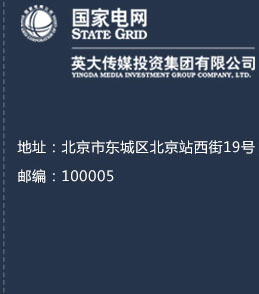【人物】周建斌:挖掘农林生物质的绿色价值
文/本刊记者 张琴琴
走进南京林业大学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周建斌教授的办公室,记者一眼就注意到桌上放着的一包核桃壳。
“刚出差回来,路上吃剩的果壳一般我都会包好带回来,这可是上好的生物质炭原料。”周建斌指了指办公室地上的几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最近随手收集的核桃壳、杏仁壳等,“攒得差不多了,就拿到实验室去用。”
随手打包果壳的习惯,被周建斌自嘲为“职业病”。废弃物果壳,在研究了大半辈子生物质的周建斌看来,有着多种再利用价值:可发电、可供热、可做活性炭,还可做肥料……
呼吁要正确认识生物质
何为生物质?广义上,生物质是指利用大气、水、土地等通过光合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有机体,包括植物、动物及其粪便和微生物。狭义上,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稻壳、枝条、农林加工下脚料及农林废弃物等。
周建斌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农林生物质,农业生物质的代表有秸秆、果壳等,林业生物质的代表有城市园林修剪残留的树枝、树叶等。
生物质曾一度被误解为高污染燃料。虽然生态环境部多次明确“生物质燃料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但社会上对生物质的偏见和误解依旧存在。
研究生物质近40年,周建斌一直在呼吁,“要正确认识生物质”。
在周建斌看来,生物质能是天然的碳中性能源,安全、稳定,能有效替代化石能源,也具备产业化前景,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可再生能源。
地球上生物质能总量达1600亿~1800亿吨/年,相当于世界总能耗的8倍。在周建斌看来,若农林废弃物不合理利用,任其腐烂发酵产生甲烷,其温室效应将是二氧化碳的20多倍。2021年9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表明全球枯木每年释放超过399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化石燃料排放量的1.15倍。这些生物质若不合理利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甚至引发森林火灾。
国际上,生物质能已经占发达国家能源体系的较大比重。国际能源署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生物质能在可再生能源终端市场的占比超过50%,是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的总和;在欧盟可再生能源市场中,生物质能占比超过65%;在可再生能源供热市场中,生物质供热占比超过90%。
为生物质正名,就要撬开其绿色价值。
“吃干榨净”农林废弃物
生物质的使用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周建斌以秸秆为例进行解释:“焚烧秸秆会造成空气污染,大家已经有体会。有专家建议‘秸秆还田’,把秸秆埋入土里,自然发酵做肥料使用,殊不知这样既产生沼气又产生新的病虫害。我认为,利用秸秆的最好方法,是先把它的能源效益发挥出来,同时得到秸秆炭和醋液作为肥料使用。”
要“撬开”生物质蕴含的绿色价值,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2002年,在张齐生院士的指导下,周建斌带领团队开发了“生物质气化热、电、气、炭、肥多联产技术”并实现产业化,探索出了一条农林生物质利用“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就是通过特殊的专利技术,把农林废弃物(秸秆、稻壳、果木枝条、果壳、木屑、木片及园林绿化废弃物等)气化,同时产生生物质可燃气、生物质炭和生物质提取液。
这一技术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替代煤炭和天然气,可以用来发电、供锅炉燃烧供热;生物质炭根据原料的不同可以分别加以高附加值的利用,木本植物可以用来生产活性炭或者工业用炭或者机制烧烤炭,禾本植物的竹类原料可以生产竹炭,也可以加工成竹活性炭,而禾本植物的各种秸秆,则可用来生产炭基肥料;生物质提取液(俗称木醋液)能作为消毒、杀菌材料或者液体肥材料等。
“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吃干榨净’农林废弃物的每一分价值。”周建斌形象地解释。
生物质多联产:减碳、增效
评价一项能源技术好不好,有两个维度:能不能帮助企业降碳,能不能让企业盈利。
对于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周建斌也向记者做了这两方面的估算。
减碳方面,按6兆瓦生物质发电多联产项目计算,一年可利用8万吨左右的生物质原料,每年发电达4200万千瓦时,节约煤炭1.6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万吨,减排氮氧化物123吨、二氧化硫400吨。同时,可得到1.6万吨生物质炭,生产8万吨炭基肥料。这1.6万吨生物质炭,又可以固定二氧化碳5万吨左右。
经济性方面,周建斌以河北承德项目为例做了说明。
河北承德地区是全国杏仁壳集散地、果壳活性炭产业中心。传统活性炭技术生产1吨活性炭需烧煤2吨,活性炭产业也被定性为三高产业:高成本、高污染、高能耗。且承德地区属于三省交界地,气温低,供暖时间长、需求大,宾馆浴室小煤炉多。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该地区采用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建成了“杏壳生物质气化发电联产活性炭、肥、热”项目,淘汰了市区宾馆浴室小煤炉。该项目每年发电2100万千瓦时,按0.75元/千瓦时电价计算,价值1575万元;生产活性炭6000 吨,价格按9000元/吨计算,价值5400万元;供应热水(80 ℃)20万吨,按照热水单价20元/吨计算,价值400万元;产生提取液2600 吨(生产液体肥约4970吨,单价5000元/吨),价值2485万元。总产值约9860万元。
谈及这项技术,周建斌是自豪的:不需要外加能源,也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药品、添加剂、催化剂,同时生产可燃气、生物质炭、生物质液,并可分别进行高值化利用,且生物质中的碳、氮、硫等污染性元素大部分保留或者固定在生物质炭和生物质液中,没有像生物质直接燃烧一样排放到大气中。
他接着算了一笔大账:“我国有18亿亩耕地(年产秸秆10亿吨左右)、42亿亩林地(不包括城市、道路、小区绿化)、40亿亩草地(林草百亿吨),如果把林业当作农业来做,每年可再生的量达百亿吨以上。将100亿吨用于气化多联产技术与产业,可发电约8万亿千瓦时(约等于目前我国全年用电量),减排二氧化碳约80亿吨,同时生产生物质炭20亿吨,固定二氧化碳约60亿吨,总减排二氧化碳约140亿吨,相当于我国全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这对我国甚至世界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绿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命运的安排”
“作为研究人员,一辈子能找到好的研究方向不容易。”探索研究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于周建斌而言,多少有点像是“命运的安排”。
六朝古都南京钟山脚下、玄武湖畔,矗立着一所高等学府——南京林业大学。1985年,周建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该校林产化工系的林产化工专业,并在毕业后留在该校林产化工系热解教研组。没两年,他又在本系继续深造,于1995年从南京林业大学生物质热解与炭专业硕士毕业。
2001年,工作多年的周建斌想把活性炭与生物技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了继续深造读博的想法。恰逢张齐生院士(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学专家,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在做竹炭研究,周建斌的生物质热解与炭专业背景与此极为契合,经时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余世袁牵线,周建斌报考到张齐生院士的门下读博,同时兼任南京林业大学木材热解与活性炭教研室的主任。
从2002年相识到2017年张齐生院士去世,周建斌一直与张院士共事。张院士指导和支持周建斌以竹炭研究为起点,并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研究农作物秸秆炭,再到生物质多联产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
“当时的竹炭(包括木炭)几乎都是采用土窑烧炭技术,污染大、耗时长、得率低。在张院士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用大型干馏法制备竹炭。由于干馏法是需要外加热的,张院士就提出能不能不加外热生产竹炭?”带着这个问题,周建斌结合此前所学,带领团队多次实验,与张院士反复探讨,形成了后来的生物质(竹子、木片、秸秆、稻壳、果壳)热解气化联产炭(竹炭、木炭、秸秆炭、稻壳炭、果壳炭)、肥、热技术,比欧、美、日、德等西方国家的同行们整整早了十三年。
新技术问世,要直面各方的质疑,也面临如何推广的问题。此后多年,为向全社会介绍生物质多联产技术,张院士倾注了大量心血,周建斌多次跟随张院士去全国各个大学、研究院所交流该技术。
这项技术在2018年获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届科技成果发布会的五大成果之一,获得了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并在2021年获得由科技部主办的首届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优秀奖。如今,生物质多联产技术在江西、湖南、云南、安徽等地都有项目落地,实现了工业化。
2022年,凭借生物质多联产技术,周建斌被评为俄罗斯工程院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理论上生物质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周建斌看来,生物质能的发展还是偏慢。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一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2.58亿千瓦,常规水电装机3.68亿千瓦,抽水蓄能装机4699万千瓦,风电装机3.76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4.25亿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4195万千瓦。
相对于国内的火电、燃气发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总装机规模小,占比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会资本对其投资热情较低,对此,与企业打交道甚多的周建斌深有体会:“本身就做活性炭或者化肥的企业,更有意愿投生物质多联产项目。有大型企业找我咨询过生物质能的技术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张齐生院士生前曾经教导周建斌“三要做”:国家需要的,要做;企业需要的,要做;老百姓需要的,要做。周建斌牢记恩师的教诲,借着各种机会积极推动生物质能发展。在周建斌办公室的书架上,珍藏他的大学专业课本、很多省市领导与他关于生物质能源多联产专利技术推广的通信函件,以及2003年以来他参加全国各种生物质利用、生物质能源、肥料方面会议的照片、影像资料、会议文件,还有各种媒体关于生物质气化多联产的报道。
教书育人数十载,周建斌也一直鼓励学生利用好在校的黄金时间,踏实搞研究;并在学生毕业时安排他们去工厂实习,“只有接触企业,了解实际需求,未来才能做有用的研究”。